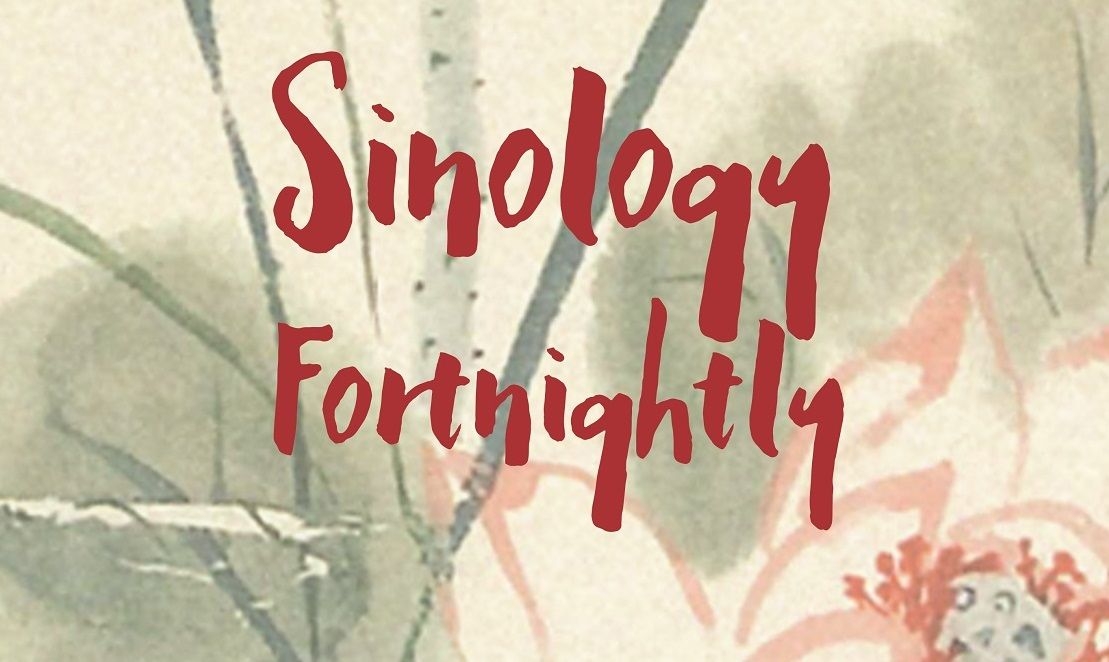
為促進校內國學與漢學交流,饒宗頤國學院專門開展「半月譚」活動,每半月邀請一位本校或校外國學與漢學專家分享其獨特見解。歡迎有興趣者參加。
語言:英語
大要(常慧琳紀錄):
作為開場,史蒂文森博士使用了一系列圖片展示青海藏區的特殊風貌,這些圖片皆是他多年考察積累的珍貴資料。史蒂文森博士介紹道,就美術史的概念而言,直到近代所有的藏族美術均為宗教美術。在1958年至1978年期間,藏族傳統美術活動因此宗教性質被禁止。後來禁令漸鬆,當地開始重建因毀壞而關閉的寺院,傳統美術活動也同步恢復。
史蒂文森博士認為,當我們去思考、去理解藝術發生了什麼,或者什麼發生在藝術上,我們首要的關注點應在於「它在哪裡」以及「誰關注它」。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見青海藏區藝術出現了新的視覺表達形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藏族社區藝術活動的範圍不斷擴大,至少有四個發展方向:其一,服從宗教生活復興的需要,此可以從「五屯藝術」在北京的展出(1982年)觀察到,這一次展覽是單一的佛教主題。但從展出座談會中大家的討論來看,多數學者認為此次展覽品類有限、主題單一;作品反映的是藏區人民不再需要的生活方式;是落後文化時代所產出的獨特藝術作品。是以另外三個發展方向:服從國家政治方針的要求、追隨國際前衛藝術的要求、反映地方生活的公共藝術(非宗教的、非傳統藝術的)也愈獲重視。由此,史蒂文森博士不禁發問:如何處理藏區及其多元性?當代藏區藝術(contemporary Tibetan art)與藏族社區(Tibetan communities)的關係如何?從80年代的Mkar mdzes and The New Tibetan Painting、90年代的Brtson grus rab rgyas’s Great Thangka和千禧年的Don grub tshe brtan’s Street Art可以看到革新背後的邏輯在於內容的替代、規模的增大與位置的變化。史蒂文森博士用甘孜新藏畫(The New Tibetan Painting)來舉例,佛陀的位置被代以當代政治人物,格薩爾代替了彌勒佛的位置,體現了「藏漢一家」的政治主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一幅長達618米的唐卡作品上。史蒂文森博士並重點介紹了優秀青海藝術家Gser brag don grub tshe brtan,他並非熱貢人,但他將熱貢視作一個最佳的當代藏區藝術與其社會文化的對話地,致力於在藏族社區中尋找一片藝術的棲息地。當然,他並不是站在宗教藝術的對立面,而是希望其他藝術形式、非精英的藝術可以安靜地在社區成長、討論與實踐。
討論階段,常慧琳小姐提出了對藏區藝術的界定與當代藏區藝術發展的相關問題,史蒂文森博士認為,當代的任何藝術形式必定受到時代的影響,藏區藝術並不僅僅只擁有其民族身份,除了唐卡之外也可以有其他題材的藝術形式。美術傳統應當在不受到政治強迫的狀態下與時代一起求新求變。應聽眾的要求,史蒂文森博士還講解了藏畫的特點,他提到,藏畫的光源並非如西方油畫所習慣的左上方或右上方,而多是由人物內部發射而出的「神光」,讓聽眾饒富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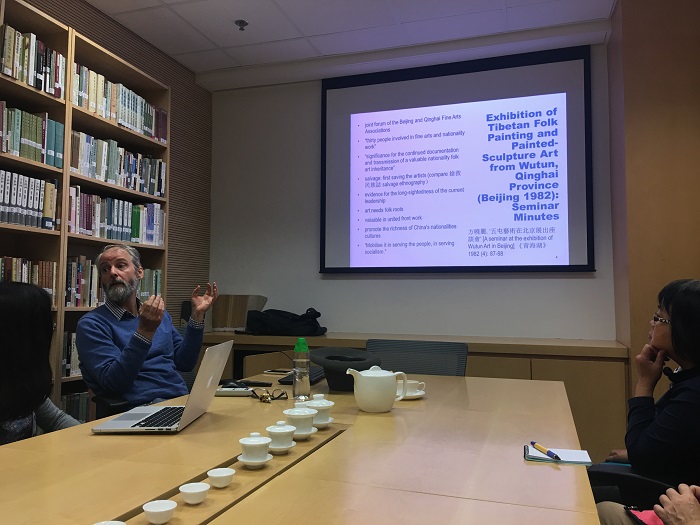
大要(林怡劭紀錄):
本次講題,乃是以文化研究的視角切入,吳存存教授開頭便為我們點出此領域研究的一個重點:必須時時注意中西文化的差異,不能直接以西方的概念硬套中國傳統的同性戀現象。在演講過程中,吳教授不停強調此點,為我們從理論角度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男風研究在意義、方法上的思考。
整場演講提出了幾個基本討論面向:
一、 同性戀的定義問題。
二、 中國傳統社會是否承認同性戀?
三、 宗教背景與影響。
四、 法律上的問題。
五、 同性戀之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家庭觀。
六、 社會階層和同性戀關係中的主動和被動方之深層意涵。
七、 中國傳統社會中關於同性戀的傳統文獻。
吳教授提到,雖然說同性戀,其實主要指男性,因傳統中國社會關於女性同性戀的紀載十分稀少。而在西方的定義之中,同性戀是兩個天生同性者在平等、自主的情況下相戀,但傳統中國的同性戀卻往往地位不平等,故此有部分西方學者並不承認傳統中國的男風為同性戀現象。吳教授便慧黠地反問:那麼傳統中國有異性戀嗎?事實上,不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這兩個詞彙的產生都相當晚,甚至異性戀主要是因同性戀此負面詞彙產生後才創造出來。是故,若依西方定義稱傳統中國沒有同性戀,無疑荒謬。
法律問題也是同性戀議題中重要的一環。吳教授指出,西方由於過往視同性戀為罪,故他們特別關注法律上的相關問題。當他們研究傳統中國的同性戀現象時,亦自然而然從法律角度切入,便發現情況全然不同。如《大清律》中記載幾則同性之間的強奸案,便曰「例無專條,自應比例問擬」,也就是說,官員往往比照異性之間的強奸案件以判。
至於同性戀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婚姻、家庭之關係,更非一種敵對的位置,而是處在婚戀的邊緣。某些時候,傳統中國文人習於將男性之間的感情浪漫化,視為純粹的愛情。舉例來說,幾名有斷袖之癖的文人,他們自身亦都會有妻妾,甚如陳維崧還幫情人徐紫雲納妾,而作〈賀新涼〉(小酌荼蘼釀)一闋詞,表達了徐紫雲婚禮當天詞人的微妙感情。也就是說,傳統中國人將婚姻視為人生的義務,以傳宗接代為要,所謂「婚姻是愛的結晶」這種觀念,要遲至20世紀才產生。是以男風行為並不會影響家庭和諧,而且是很正常的狀態。
然而吳教授也強調,雖然傳統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寬容,卻絕非進步,事實上這之中依然存有權力關係與歧視,如主動方與被動方予人之觀感全然不同,被動方被稱為「兔」,主動方則被稱為「大老官」等等。總而言之,大家需要更加理解傳統中國在同性戀現象上的幾個獨有特點,才能進一步發掘出背後的文化意義。

日期:2018年2月23日(星期五)
大要(常慧琳紀錄):
朱夢雯博士介紹到,此次講座是摘取自其博士論文 “Half-Dead But Half-Aliv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in Late Sixth-Century China” 之Chapter 3 “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的一節。其博士論文主要圍繞著南北朝後期文學與文化伴隨著戰亂與遷移的發展演變展開探討。在這一時期的文人群體中,庾信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在演講中,朱博士先介紹了庾信的生平、著作及後人評述,給了聽者一個整體把握,接著重點以〈小園賦〉為個案考察對象。〈小園賦〉(Rhapsody on Small Garden)是庾信隱逸主題的代表作。按照現代注解本,〈小園賦〉全篇可以分為五個部分,朱博士帶領大家誦讀了各段文字並進行文本細讀,對庾信在賦中頻繁使用的歷史典故進行細緻觀察。她發現在〈小園賦〉中,主體部分中有大量對陶淵明(ca.365–327)的化用、引用。這樣的用典情況在與庾信相關的詩歌作品如〈寒園即目〉、〈臥疾窮愁〉和〈歸田〉等的對讀中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來。講者觀察到,〈小園賦〉的首尾段落都呈現出頻繁堆叠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典故。這是庾信入北後文學寫作中常用的手法,用典的結果往往形之於一系列的文學人格。朱博士提出:這裡的頻繁用典已經超越了單純的修辭手法,而成為作者精心選擇、營造和比附的自我表現方式。庾信文學作品中的這種「自我表現」正是其被迫由南梁(502–557)而入西魏(535–556)、北周(557-581)後文學轉變的重要方面。講者指出,在〈小園賦〉的末段,庾信的用典更是超越了「隱逸」的範疇,而涉及到蘇武、荊軻這樣與其真正的「歷史自我」有著相似遭際的歷史人物,從而使作者在歷史中的人格形象與賦中所塑造的「隱者」形象產生曡合與混淆。那麼,庾信是否真如其在《小園賦》中所記述的那樣,曾是一位隱者呢?現存的史料和相關文獻中並沒有庾信歸隱的記載,因此我們不能簡單根據其文學作品來比附其真正的歷史自我。她進一步討論了文人之「歷史自我」與「文學自我」二者間的距離,認為以刻意塑造「文學自我」為特色的「自我表現」在中國六世紀晚期文學變遷中所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一位長者詢問朱博士何以選擇這一篇賦作為切入?朱夢雯博士解釋道,這是庾信入北賦中的典型,有十分強烈的特色並且是她最喜歡的一篇。老先生還感慨〈小園賦〉用中文閱讀便已足夠佶屈聱牙,何況是用英文,又與朱博士討論了〈小園賦〉的英譯問題。朱夢雯博士認為有一些譯本太過直譯,有失達雅,希望在未來可以翻譯庾信全集,使詩歌重新成為詩歌。有同學亦對朱夢雯博士的博士論文標題“Half-Dead But Half-Alive”很感興趣,朱夢雯博士介紹道,庾信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枯樹賦〉表現了他在北朝時的狀態;其他入北文人也提到了「半生半死」的意象,所以以此為題也反映了由南入北的文學轉變。有聽者提問,〈小園賦〉中庾信大量追述了陶淵明,但陶淵明在文學史中的地位是在宋以後才被確立的,這樣透過用典向陶淵明靠攏的情況,在同時代入北文人中是否為一普遍現象?朱博士肯定了陶淵明的接受史,但她指出,雖然當時由於宮體詩的流行,陶淵明的風格可能並不是主流,但早在庾信身仕南朝時,與其密切往來的蕭統便很喜歡陶詩,還曾為之編寫文集;北齊陽休之也曾在文集散佚後重新編寫。可見不論南北,當時文人對陶淵明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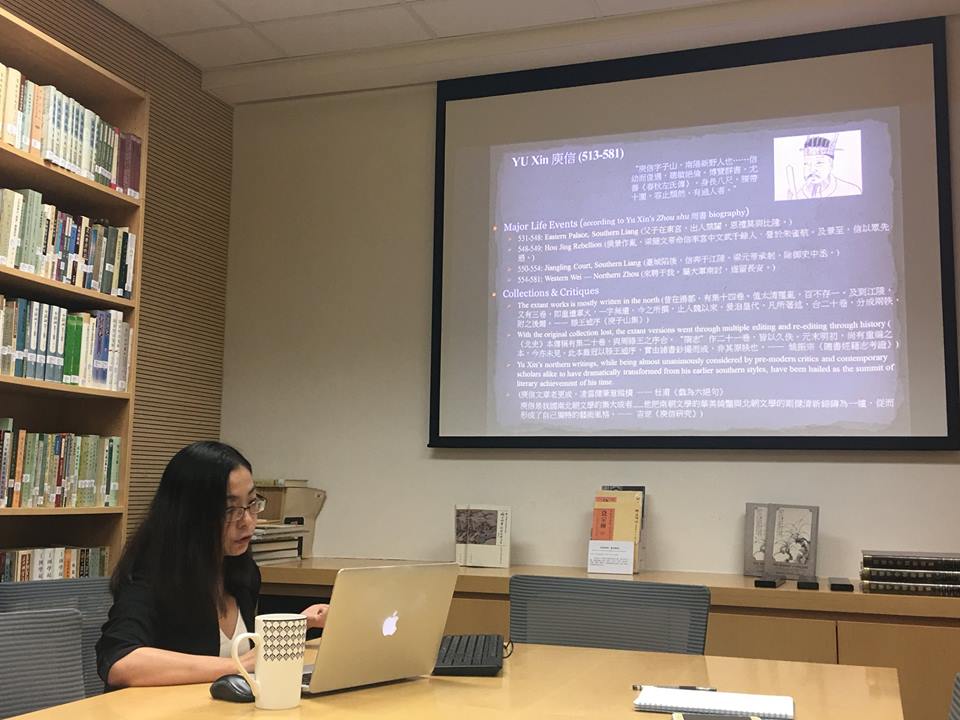
日期:2018年3月23日(星期五)
大要(朱夢雯紀錄):
梁教授首先從他正在寫作的一部專書 “Why History Mattered: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a” 談起,提及這部書中所集中探討的歷史成爲早期中國政治論辯中一種特殊語言的問題。梁教授在研究中,將視角擴展到這一階段傳統史學史研究所慣常使用的文本材料之外,更廣泛地關注到如《詩經》,金文,諸子,漢人著述和出土文獻等多方面的材料,《楚辭章句》便是其中之一。梁教授與我們分享的這一研究,也是他在去年匹茲堡大學“Designing Space: The Exercise of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in Pre-Modern China”會議上發表並被收入會議論文集的一篇論文。
談及《楚辭章句》,梁教授首先指出這部編集與《淮南子》等其他一些作於秦漢之際的著述一樣,體現出對“空間”的特別關注。他援引《淮南子》和《老子》中論“道”的語詞進行比較分析,指出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具有的時間性相比,《淮南子》更從空間向度上界定“道”,而同樣對“空間”的自覺亦呈現在當時的大量文學創作中,如賈誼《鵩鳥賦》,《弔屈原賦》,司馬相如《大人賦》,《上林賦》,尤其是《楚辭章句》中。在對《楚辭章句》一書源流做出簡要梳理後,梁教授提出無論是“楚辭”作為一個專有名詞還是其代表作家屈原,都不見於漢代以前的文獻。依據現存文獻資料,“屈原”之名首先出現在賈誼《弔屈原賦》中,而對“楚辭”的關注也是在漢代才逐漸展開而達致興盛。在此基礎上,梁教授帶著大家對《楚辭章句》中<離騷>,<遠遊>,<懷沙>等篇章中的片段進行細讀,並著重解讀了其中主要表現為“空間錯置”的空間特徵。與之相對,梁教授亦舉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封禪刻石等具有宮廷寫作性質的文本,指出其中所極力彰顯的完善的空間秩序。在最後的總結中,梁教授歸納了三個方面的研究發現:第一、在秦漢帝國崛起的時期,開始產生大量的空間敘述。第二、《楚辭章句》體現出一種錯置混亂的空間。第三、與《楚辭章句》形成對比的,是秦漢之際宮廷書寫中對完善的空間秩序的極力渲染。
